我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修建的第一座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世界首座六线高速铁路大桥南京大胜关长江大桥,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杭州湾跨海大桥……这些大名鼎鼎的桥梁,都由中国中铁大桥局设计建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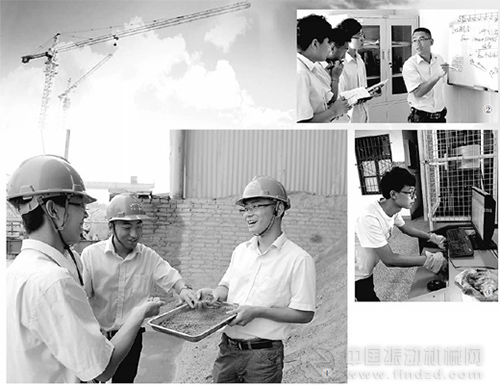
图①:藕长洪(右)在教试验人员如何初步判断砂子的质量。 图②:藕长洪在讲解混凝土配合比计算方法。图③:付少英正在进行钢筋试验。
在这个有着悠久建桥历史的企业里,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不直接施工浇筑,却天天泡在工地里。他们就是大桥局工程项目的试验技师。混凝土配合比是否达到施工要求?钢筋粗细、强度够不够?项目进行的事前、事中、事后,他们都得检测,合格的才能用,不合格的直接清场。9月初,记者深入工地、实验室,走访了中铁大桥局七公司试验公司的“80后”“90后”技师们——大桥质量的第一把关人。
平均年龄30岁
细心严谨第一位
“我是1992年的。”“我是1995年的。”在武汉硚孝高速公路建设工地,记者见到了两个工作不久的“90后”技师,高伟和李业刚。硚孝项目是李业刚进大桥局后参与的第一个工程项目。“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检测砂石料中那个‘砂子’。”李业刚说。
这个工地试验区,一进门就是巨大的混凝土搅拌站,站前分类堆积着小山一样的砂料、石料、水泥等原材料。李业刚成天就和砂子打交道。“别小看砂子,所有原材料里,就砂石料最容易出质量问题。有时一次来一船砂,3000吨,我得一车一车检,一点都马虎不得。”李业刚介绍,小小砂子,门道可多了,什么含磷量、堆积密度、空隙率等等指标,每一样都和工程质量息息相关。8月24日来了一船砂,李业刚连上几天夜班,从晚上6点忙到早上7点。“厂家先送样品来检,样品合格再车检、进了料仓还要检。有一次,砂子是晚上运来的,我本来抽检的砂子是合格的,第二天早上再一看,才发现夜里没看清,砂里掺有很多卵石,不合格,只能清退。”
中铁大桥局七公司试验公司经理、全国“最美青工”获得者藕长洪说:“我当徒弟时,师傅就跟我说,材料只有‘合格’和‘不合格’,决不能用‘差不多’‘可能’‘大概’这样的字眼。”现在他也是这样要求自己团队的。
藕长洪今年32岁,他带领的试验公司共33人,技师平均年龄只有30岁。他也是从李业刚这样的基础岗位干起来的。2009年,他参加了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的建设。当时,他们本已选定了几家质量较稳定的供砂企业,可是,汛期到来后,长江上所有砂场都被禁止入江采砂,他们只好重新选择砂源,砂子质量参差不齐。“那时,我检出有些砂子质量不合格,要求清场。可运砂来的货车司机不干了:我不收货,砂场就不付他们运费。司机们都堵在我门口,有的求情,有的耍横威胁,但我硬是没有松口。”藕长洪说。后来,经过协商,他同意将部分砂料用在工地边的路面上,同时改变检验方式,派技师先到砂场、石场驻点检测,检测合格了才出场,运到工地来,这才化解了矛盾。
“干我们这一行,细心、严谨是第一位的。虽然人都是毛头小伙,但做事不能毛糙。材料合不合格,我们用数据说话。我们对水泥、砂、钢筋、混凝土等出具的报告,是白纸黑字,得终生负责的。”藕长洪说。
书本知识是基础
实际操作靠创新
如果以为试验技师只是对钢筋、水泥、砂石等原材料把把关,那就错了。什么样的项目、工程的什么部位、应该用什么材质的混凝土,都由他们先研制出来。这是书本上没有现成答案的。每个答案都要通过反复试验才能完成。比如混凝土强度不够,可能造就“豆腐渣”工程;强度过高,对企业来说不经济;凝固过快或过慢,可能跟不上打桩进度,造成施工问题。还有,有的地方气温低,材料要有很强的抗冻性;有的地方水系纵横,材料要有抗渗性,等等。
2011年底,藕长洪和他的徒弟董志成参加湖北恩施州恩来、恩黔高速公路项目的建设。由于恩施地质条件复杂,建设中要开山通隧、悬崖架桥,施工难度极大。而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是,恩施本地没有河砂,假如从山外运砂进来,成本太高。这种情况下,只能使用“机制砂”,就是用当地石头磨成粉末制成的砂。但相比于河砂的“圆润”,机制砂棱角过于分明,加入到混凝土中,会影响混凝土的流动性。假如混凝土浇筑时遇钢筋阻力不能顺利往下流,就会形成“空洞”,影响工程质量。经过反复试验、配比,试验技师们终于找到了使用机制砂配制高标号混凝土的最佳方案。董志成还因此获得了全国工程建设QC二等奖。
2012年底,藕长洪进入宜昌庙嘴长江大桥建设项目。他根据设计要求反复试配,最后从近20组配合比试配中选出最优配合比,经过施工后检测表明,该优化配合比既保证了施工质量,又起到节约成本的效果。目前完成的4.4万立方混凝土,已通过配合比优化,实现节约成本96.8万元。
翻开试验公司花名册,每个技师都是大专毕业、科班出身,许多人都获得过技能大赛或技术创新的奖项。藕长洪本人获得过中国中铁第十届青年技能大赛试验工比赛个人第一名,中央企业职工技能大赛建筑材料试验工决赛银奖,获得过“中央企业技术能手”和“中央企业青年岗位能手”荣誉称号,还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我鼓励年轻人多参加技能大赛等活动,因为在比赛中,才能找到自己的差距,更有前进的动力。”藕长洪说。
全国项目到处跑
“桥嫂”辛酸谁知道
“辞职吧,我养你!”藕长洪的夫人曾放过这样的“狠话”。
和所有大桥建设者一样,试验公司的技师们常年在全国各地项目上跑,很少和家人团聚。中铁大桥局曾拍摄过题为“桥嫂”的沙画艺术微电影,看的时候,大桥局的男子汉们无不潸然落泪。
“2009年孩子出生时,我正在南京大胜关长江大桥建设项目上。半夜里,我爱人怀孕阵痛发作,给我打电话,我连夜赶火车回武汉,回来时,孩子已经出生了。”试验公司总工文沛说。1980年出生的文沛,毕业后一直在中铁大桥局四公司工作,干的也是试验检测。他家在武汉,可项目大多在外省,所以一年只能回家2—3次。“有时候回家,孩子不让我进房间,哭着说‘出去出去’!因为把我当成是陌生人啊!”说着,文沛有些哽咽。
2012年,七公司试验公司要用人,文沛这才申请调回武汉。可即便公司在武汉,但由于项目遍及湖北各地及周边省份,文沛现在也只能一两周回家一次。“孩子现在和我感情好些了,但也比不上别人家的父子亲。”文沛说。
“从结婚起,我爱人就经常对我说,辞职、辞职,希望我在家附近另外找工作。”藕长洪说。武汉三环线三金潭立交工程开工半年后,藕长洪家要装修婚房,可工地正值现浇箱梁、粉喷桩大面积铺开,正是最繁忙的时候,最终,婚房装修,他只回去了一天。以后,围绕辞职问题,藕长洪不断地做妻子的思想工作:“我学的就是这个,干的就是这一行,事业发展得也不错。我回来做什么?难道卖服装去?”久而久之,他的妻子像所有“桥嫂”一样,经历了从“谅解”到“理解”到“支持”的心路历程。
而25岁的小伙子毛勇,还没有女朋友。他发愁的是“生活圈子太小了”。毛勇是四川人,2013年从西南交大毕业后,来到七公司试验公司。一上来就进了太远北中环桥建设工地。7月开工,12月通车,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建桥速度。建设者们必须“吃3睡5干16”——吃饭3小时、睡觉5小时,工作16小时。“就一个字,‘累’!不过,也能学到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技能,很充实。”毛勇说。工地上基本是男子汉,很少有女性,而工程结束回到武汉,整个试验公司也只剩4个人,其他人都在各地项目上。“有时晚上下班了,真不知道干什么好,孤零零一个人,觉得还不如在工地上,年轻人多,聊得来。”
“做个‘大桥人’,就是挺自豪的事。我们的小伙子,基本都结婚了,不愁对象!”藕长洪乐呵呵地说。也许,找个“桥嫂”并不难,但“桥嫂”为桥梁建设的付出,不是谁都知道。
















